这是最近新学的一个词,下午查了一下工作的地点,不折不扣的把这个词用上了,如假包换的活学活用,在GE上找到那一大堆排的整整齐齐的测试车辆跟那对夹在两个测试车间中间窄窄的篮球架,顿时感觉晴天霹雳在背后闪过,哗啦啦闪黑了电脑屏幕,两眼一抹黑,涕泪横流,生不如死。那设计院都跑到钱塘江的入海口去了,钱塘江潮稍微涨涨就能把那地方淹了,开车一不留神就能开回绍兴去,难怪他们说自己大多数员工都住在下沙,技术支援部的部长说上班通勤车半小时到公司——从下沙到那鬼地方当然是半小时足够啦。原本还以为不会离市区很远,现在随便指个地方直线距离都是十五二十公里,那还是算少的。
这下好,头一个月工资不用买自行车了,老实攒钱买车。
前阵子写了窒专栏的第一篇,因为找不到以前那些照片的缘故,醒悟这六年没拍过一些够得上台面的照片,于是昨天特意回去大一的校区,顺便在一些街道和市井捕景,以后可以用在文章里。
WordPress有个很招人烦的毛病,相机上下来的照片一般是按照拍照时间顺序命名的,上传的时候也按照排在前面的照片先上传,偏偏插入图片的时候是排在后面的图片跑到文章的最顶部,原本顺溜溜的一串,都被倒撸过来了,很不爽,还得重新手工排序。昨天去的时候下着小雨,带把伞,蛮好,一者下雨照片出来色泽会润一些,亮色会更鲜艳,二者是遮人耳目,一个研究生要毕业滚蛋的人回到大一的校区,有些怯生生。景物依然在,人物已然无踪了,楼还是那几栋楼,松还是那几棵松,一抬头望见那栋白楼,这种滋味叫触目惊心——楼顶那长长一条“建设国际知名××××”的大红横幅哪去了?难道学校也知道挂出来丢人了?

其实当年在这边的时候这个路口是没有红绿灯的,照片的左下角有个白色招牌,上面写的是同视眼镜,上一架眼睛,是从这个店买的,价钱很实惠,那架眼镜戴着不太会感觉眼睛干涩。这间眼镜店往东的一间店面,原先是间理发店,是我到了大学时候才开的,之前开的什么店忘了,手艺蛮不错的——应该比臭名昭著的小义强多了吧?再往东就是学校的大门了。同视眼镜门面的西边,是一串杂事店,小屋麻辣烫,还有一间烧卖铺,都是鼎鼎大名的——但是我从来没去过,我常去的是街对面的永旺。校门口常年有蹲着两个卖电话卡的,校门出来左拐就是,晚上似乎也来。晚上来的还有一个烤羊肉串。
这个花圃叫做郁园,每年栽花,都是园丁的活。
其实校门口的这片这片绿地上原本是有几个石膏动物的,几只梅花鹿——干嘛给刨了?干嘛给刨了?

不知道别的学院的学生有没有制图,应该是有吧,反正机械是跑不掉的。那时候,现在依然,制图室在白楼一楼,西边的几个教室,昨天去的时候一个制图室里面几个学生在自习,没有不是画图。这个关着门的教室里里面放着几张A0纸,我只敢偷偷的张望一眼,期末了,他们应该是画个减速机——我只得了80分。不过现在还是常常在学校里碰到和蔼的黄老师——一栋办公楼的嘛。
大一的时候不怎么喜欢自习,图书馆来的不多,不过记得很清楚当时买了一件班尼路的雨衣,柠檬黄,穿着去过图书馆。

这里原先是一楼的自习室,当时被复变函数逼得要上吊,就在这里看了两天书,后来考了七八十分,究竟多少忘了。
三楼的自习室还在, 情侣们应该都记得这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一般约会都比较喜欢这个自习室,而是一楼的那个。一楼和三楼的自习室都是靠图书馆的西边,图书馆西山墙外立着一架楼梯,从三楼一直掉到一楼,从自习室的那扇门出去就可以下楼梯,夏天是经常开的。
这就是西山墙外的室外楼梯。
特意回到白楼的西阶二,那是当年上高数课的地方,没敢进去,看到一个妞,想说“嘿,妞,我一无所有,你何时跟我走?”没敢。
看着这条道,依稀很能看见军训四连8班的身影,还有那个年轻瘦小的教官,他是黑龙江人,一个普通的士兵,用力想了很久,只想起他名字里有富字 ,我们班副叫姚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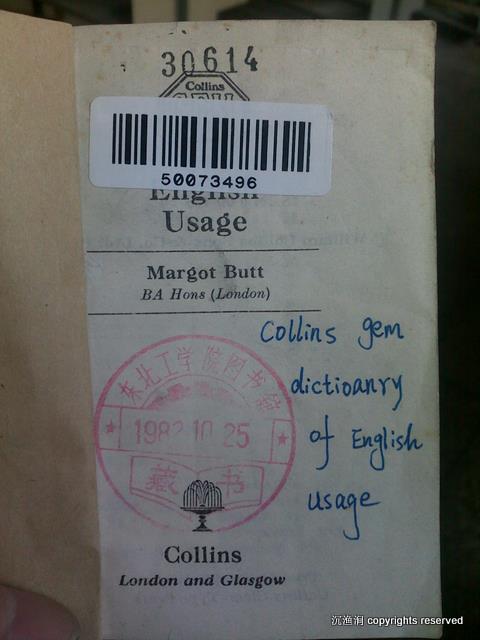


Recent Comments